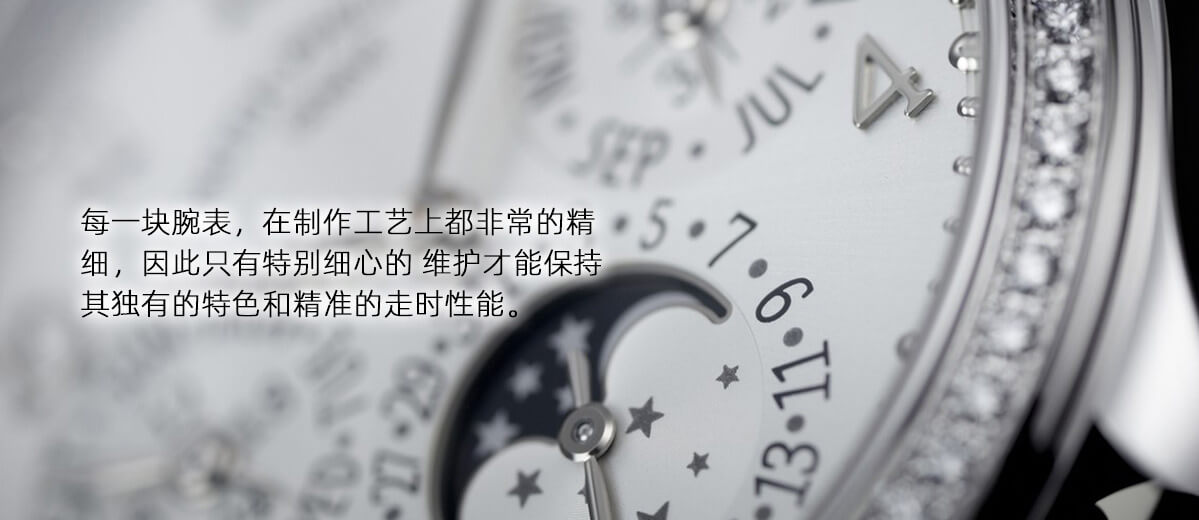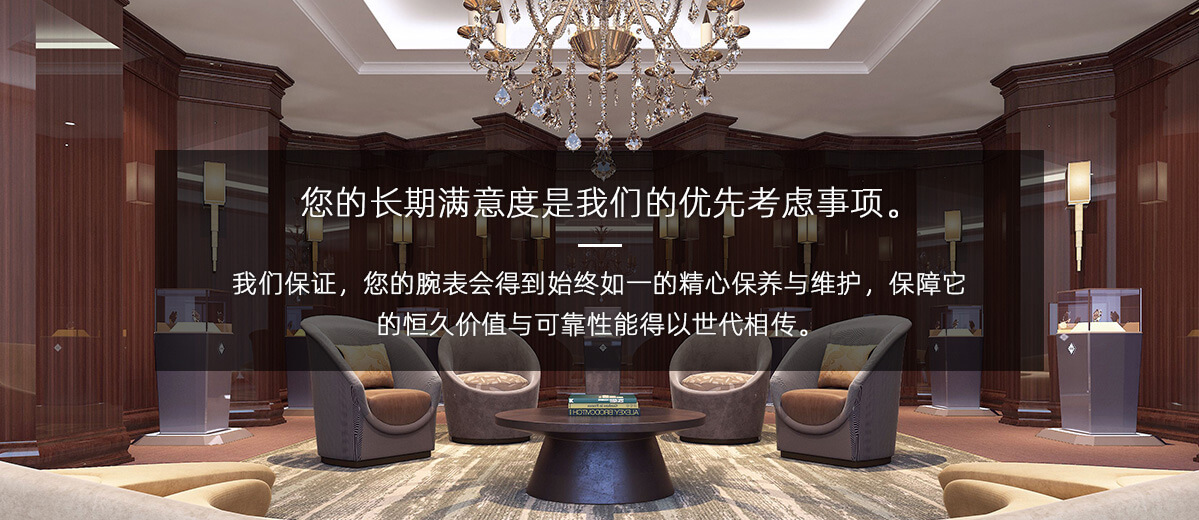用流量換奢侈年
過五十,變得很嘮叨,有些事掛在嘴邊,往往不經大腦過濾就順口而出。譬如我的朋友們可能聽過一百遍的成年往事,我還在一遍遍地復述。老了真可怕!
有一件我親歷的事,即使我知道大家都聽過了,還是會堅持再講一遍:1994年,我和當時寶璣的老大Francois Bodet站在南京路西藏路口的天橋上,看著下面如潮涌的人流,他告訴我:“這些人,都和寶璣沒關系,我不用去認識他們。

今天,還有哪一個CEO敢這么說?無論三大天王,還是五大豪牌,或是十大名表,沒有一個老大敢說一樣的話!
我自己的生活很簡單,譬如西服、皮鞋,我都只買一個品牌,只是因為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尺寸,而且這兩個品牌也不怎么潮,平時店里人也不多,還都是我看得慣的朋友們經常光顧的地方。我自認為沒有必要和太多人共享同一購物平臺,尤其是那些看上去就渾渾噩噩的人們,這一點自高自大還是要有的。
可是有一天,我發現我的西服品牌在奧特萊斯開了折扣店,皮鞋廠家在流行網站上推出了官方頁面。盡管他們給我們這些忠實老客戶種種解釋,說是奧特萊斯只是協議貼牌廠的產品,網站上不包含經典款式等等,好吧,反正之后我一套衣服一雙鞋都沒買,往后么辦?我也不知道,就知道眼下蠻省錢的。
今天,是流量為王的天下。賣牙膏的講流量,賣肥皂的講流量,賣名表的追的還是流量。各種品牌心急火燎地趕去巴結面孔沒有鞋底大的小鮮肉,惹得廣大農村青年血脈僨張,無心務農,結果弄得泱泱農業大國還得去美國買豆子。
流量到底能換回什么?從大數據來看,流量肯定能帶來一些銷量,比率再低,轉化率還是存在的。奢侈品,尤其是華貴鐘表和珠寶,首先強調的是個性和專屬,然后才是廣泛的認同。這如同農耕中的精耕細作,先把自己祖上圈好的地種好,把資源發揮到頭,然后再一圈圈慢慢擴張。文革期間,家父曾在奉賢的“五七干校”負責墾荒種地,剛到灘涂時,當地農民都在看好戲,看這幫讀書人如何改造自己。可是不久,人們就發現“干校”的農場中巴掌大的田里卻種出了最好的蔬果和最高產的水稻,紛紛前來取經。全國最好的化學家配的有機肥、最好的數學家算的秧苗比率、最好的物理學家規劃的避風角度、最好的建筑學家設計的灌溉渠、最好的生物學家制定的混合種植,還有“梁祝”的作者和演奏者每天在田邊拉琴練聲,這樣的豪華陣容,怎么可能種不出最好的農作物?
現在的奢侈品牌在營銷上集體轉向大數據,就如同放棄了精耕細作轉而使用飛機播種,即使大多數種子被扔在了屋頂、水塘和柏油路上,只要那些彈落到石板縫里的能夠發芽,還是會有收獲的。只是,這樣的收獲能夠持久嗎?
我們看到,貴價品牌都在降低入門產品的價格,為的就是迎合新客群,非傳統客群的需要,
不過一旦低價位的新品受到歡迎,必定會降低品牌的平均受眾人群的定位。人們常把奢侈品市場比作金字塔,把在塔尖的那部分品牌描述為極高端極小眾頂尖品牌。如今這部分頂尖品牌紛紛開始下探更廣更低端的客戶群,當然會找到一些受寵若驚的新客人,問題在于,這么一來頂尖的老客戶還能保得住嗎?
如果我自己也能算是一位在金字塔頂端的老客戶,到今天我已經把好幾個曾經一往情深的品牌從我的選購清單上劃掉了,這無疑很痛苦,也很快樂,因為省下的預算,能讓我開心好幾年。
以上問題均由手表維修中心提供如需轉載,請聯系管理員。
全國服務中心
WATCH MAINTENANCE
- 華北地區
- 華東地區
- 華中地區
- 華南地區
- 東北地區
- 西部地區
- 西南地區






-
北京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北京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天津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天津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太原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河北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呼和浩特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杭州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杭州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合肥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濟南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濟南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青島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福州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廈門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寧波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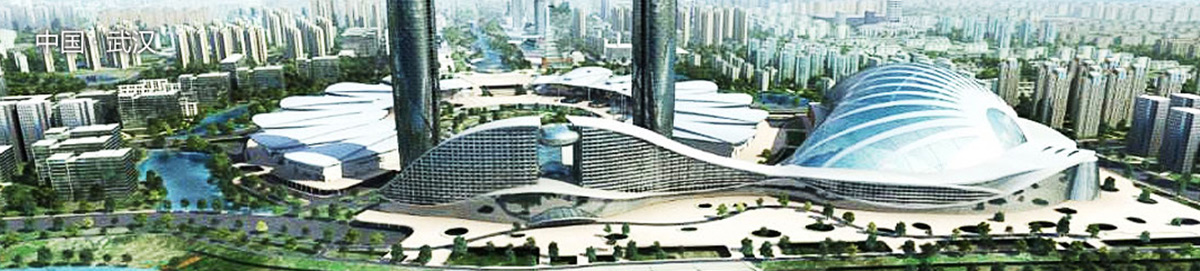

-
鄭州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武漢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武漢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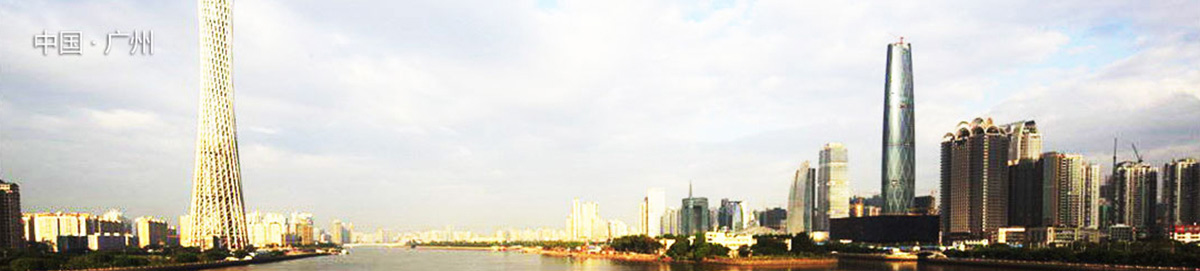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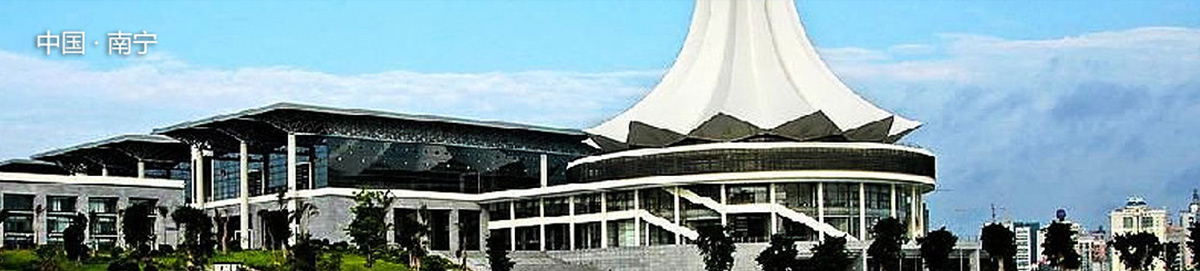
-
廣州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廣州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深圳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南寧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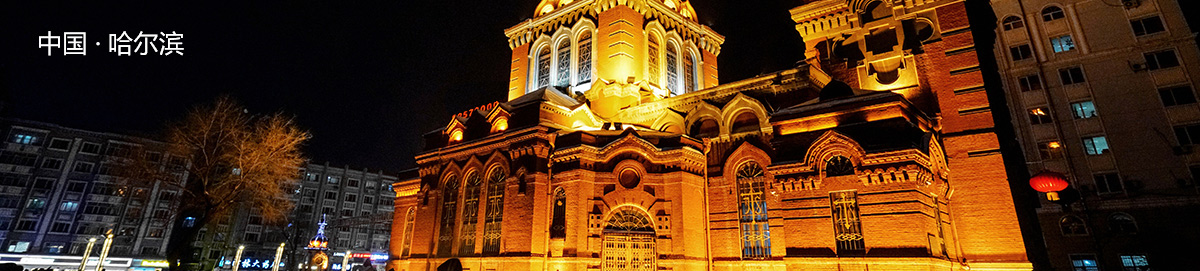
-
長春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大連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沈陽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沈陽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哈爾濱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西安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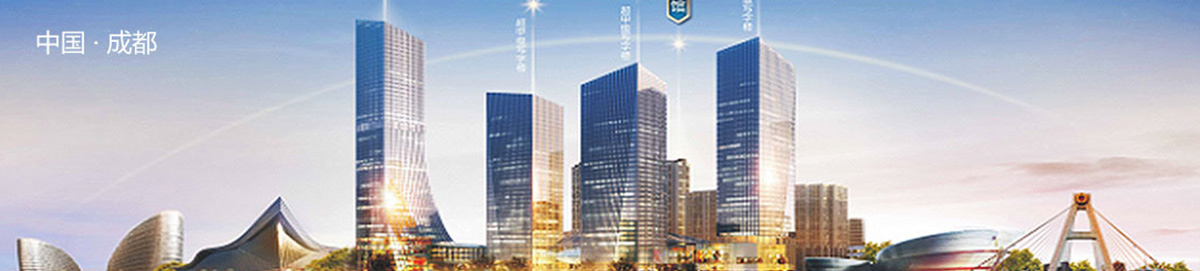


-
重慶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成都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成都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貴陽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
-
昆明服務中心
聯系電話:400-859-7757